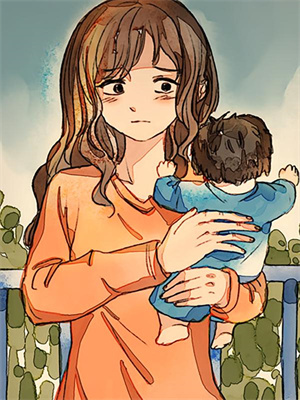简介
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本充满奇幻与冒险的历史脑洞小说,那么《重生崇祯八年》将是你的不二选择。作者“留不住就算了”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刘寅的精彩故事。本书目前已经连载,喜欢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!
重生崇祯八年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第一节 出庙
天光惨白,像浸了水的宣纸,薄薄地铺在破庙残破的屋檐上。
刘寅跟着张彤走出庙门,冷风立刻灌满了他的破衣。三月初的秦岭北麓,清晨寒意刺骨。他紧了紧腰间的草绳,目光扫过眼前的景象。
黄土。干裂的黄土向四面八方延伸,零星几棵枯树立在视野尽头,枝桠狰狞地指向天空,像垂死者的手指。官道早已不成形状,被雨水冲刷成一道道沟壑,又被无数逃难者的脚步踩踏得坑洼不平。路旁散落着破布、碎骨、干瘪的动物尸体,还有几具蜷缩的人形——已经死了,或者正在死去。
庙里陆续走出三十多人。张彤这边的老弱妇孺八人,壮汉三人组,还有十几个原本散落在庙里各处的流民,看到有人组织离开,也默默跟了上来。人群沉默着,只有粗重的呼吸和拖沓的脚步声。
“往西。”张彤指了指远处黛青色的山影,“进山。”
“等等。”壮汉——他自称王疤眼,因为左眉骨上一道狰狞的旧伤——拦住去路,“小子,你带路。还有,火折子先给我瞧瞧。”
刘寅握紧了内衬里的打火机。这东西绝不能交出去。
“王大哥,路我自然会带。”刘寅平静地说,“火折子得留着生火用。山里晚上冷,没火不行。”
王疤眼身后的瘦高个——叫赵四——凑上前,眼神不善:“谁知道你会不会把我们带进死路?火折子交出来,算是抵押。”
气氛又紧张起来。
张彤的手按在刀柄上,洪国玉和其他两个男人——一个叫陈老栓,五十多岁的老农;一个叫李石头,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——也往前站了站。
刘寅脑中飞快盘算。硬顶不行,示弱更危险。他需要展示价值,又不完全交出底牌。
“这样吧,”刘寅从怀里掏出打火机,但没递过去,而是啪地打燃,“我演示一下,证明它有用。但东西得我保管,因为只有我知道怎么补充里面的‘油’。”
火焰跳动,在晨风中稳定燃烧。
王疤眼眼睛瞪大了。他见过火镰火石,也见过用艾绒保存的火种,但这种一按就出火、风吹不灭的“洋玩意儿”,确实超乎想象。
“补充?”王疤眼抓住了关键词。
“对,里面的油烧完了,就得加。”刘寅信口胡诌,“这油是西洋秘方,我会配。”他当然不会配,但对方不知道。
王疤眼盯着打火机看了几秒,又看了看张彤腰间的刀,最终哼了一声:“行,你保管。但要是带错路,或者耍花样…”他没说完,但威胁意味十足。
“放心。”刘寅熄灭火焰,将打火机收回内衬,“大家都想活命。”
队伍开始向西移动。张彤打头,刘寅跟在他身侧指方向。洪国玉搀扶着陈老栓,翠儿抱着孩子,李石头和其他几个还能走路的妇女跟在后面。王疤眼三人走在队伍中部,眼神不时扫视四周和前面的人。最后面是那些临时加入的流民,稀稀拉拉,像一群失魂的幽灵。
走了约莫半个时辰,刘寅的腿就开始打颤。这具身体太虚弱了,胃里那半块杂粮饼提供的能量早已耗尽。他咬紧牙关,强迫自己跟上张彤的步伐。
“歇…歇会儿吧。”后面有人喊。
张彤回头看了一眼队伍。几个老人已经摇摇欲坠,翠儿也脸色苍白,怀里的孩子又低声咳嗽起来。
“不能停。”张彤声音沙哑,“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停下來就是等死。再走五里,有片小树林,到那儿歇。”
刘寅知道张彤是对的。旷野中停留,随时可能遭遇土匪、溃兵,或者更可怕的——大股流民组成的“吃人队”。
他强迫自己继续走,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视线开始模糊,耳边嗡嗡作响。
突然,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刘寅踉跄几步,差点摔倒。低头一看,是一截埋在土里的白骨,看形状是人的手臂。
他胃里一阵翻腾。
“别看。”张彤头也不回地说,“这一路,这种东西多得是。”
刘寅深吸一口气,移开视线。这就是崇祯八年,这就是小冰河期的陕西。史书上的寥寥几笔,变成现实时,是如此触目惊心。
又走了一炷香时间,终于看到了一片稀疏的枯树林。说是树林,其实只剩下几十棵光秃秃的树干,树皮早被剥光了,露出白森森的木质。
“就这儿。”张彤说,“捡柴,生火,歇两刻钟。”
人群如蒙大赦,纷纷瘫坐在地上。洪国玉带着李石头去捡枯枝——虽然树皮没了,但地上还有些断枝。刘寅找了个树根坐下,感觉全身骨头都要散了。
王疤眼三人聚在一起,低声说着什么,眼神不时瞟向刘寅这边。
刘寅假装没看见,从内衬摸出水囊——是张彤给他的那个皮囊,里面还剩一点浑浊的水。他小心地喝了一小口,润湿干裂的嘴唇,然后递给身边的翠儿。
“给孩子喂点。”
翠儿感激地点头,小心地给孩子喂水。孩子喝了点水,似乎精神了些,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刘寅。
“他叫什么?”刘寅问。
“狗剩。”翠儿小声说,“乡下娃,取个贱名好养活。”
狗剩。刘寅心里一酸。在这个时代,多少孩子叫狗剩、栓柱、招弟,可该饿死的还是饿死,该死的还是死。
“会好起来的。”他轻声说,不知道是在安慰翠儿,还是在安慰自己。
火生起来了。刘寅用打火机点火时,又引来一阵低低的惊呼。那些临时加入的流民看向他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和好奇。
有火,就有了微弱的安全感。
张彤坐在火堆旁,解下左臂的绷带。伤口已经化脓,边缘红肿,散发出一股臭味。他咬着牙,用腰刀割掉腐肉,然后用烧过的布条重新包扎。
刘寅看着,心里一沉。没有抗生素,这种感染很可能会要了张彤的命。他必须尽快找到替代品——比如大蒜素提取物?或者某些有抗菌作用的中草药?但他现在连最基本的中草药都认不全。
“张兄,我知道几种草药,或许对伤口有用。”刘寅说,“进了山,我找找看。”
张彤点点头,没说话,但眼神缓和了些。
洪国玉凑到火堆旁,压低声音:“刘兄弟,你之前说山里可能有猎户的落脚点…具体在哪个方向?”
刘寅根据原主模糊的记忆和地理知识判断:“应该在南边,靠近水源的山谷。秦岭北麓有很多溪流,猎户和采药人常沿着溪流走。”
“可咱们现在往西。”洪国玉说。
“先避开官道和主要山口。”刘寅解释,“西边山势缓,容易进。等进了山,再折向南。”
王疤眼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,蹲在火堆对面:“小子,你说山里真有野物?”
“应该有。”刘寅谨慎地说,“但得看运气,也得有本事打。”
王疤眼拍了拍腰间别着的短棍:“老子以前打过猎。只要有活的,就能弄来吃。”
“那就指望王大哥了。”刘寅顺势说。
王疤眼似乎很受用,咧嘴笑了笑,露出黄牙:“算你识相。”
两刻钟很快过去。张彤起身:“该走了。”
人群再次蠕动起来。这次,有几个流民实在走不动了,瘫在地上,哀求地望着张彤。张彤咬了咬牙,从怀里掏出最后半块饼,掰成几小块分给他们。
“吃了,跟上。掉队就没了。”他硬着心肠说。
那几人狼吞虎咽地吃了饼,挣扎着站起来。
队伍继续向西。
第二节 山脚
午后,他们终于抵达了山脚下。
眼前的秦岭,不再是远处朦胧的黛影,而是一座座实实在在的、沉默而巨大的存在。山体裸露着灰黑色的岩石,只有低洼处和背阴面能看到些稀疏的绿色——那是松柏,还有顽强存活的灌木。山脚下有一条几乎干涸的河道,河床里只剩下几洼浑浊的死水,水边散落着各种垃圾和人畜粪便。
“从这儿进山。”张彤观察着地形,“有条小路,看起来有人走过。”
确实有一条隐约可见的小径,蜿蜒着通向山腰。路上有新鲜的脚印,还有几堆灰烬——不久前有人在这里生过火。
“小心些。”刘寅提醒,“可能是土匪的哨探,也可能是其他逃难的。”
张彤点点头,拔出腰刀,走在最前面。王疤眼三人也警惕起来,赵四从怀里掏出一把生锈的柴刀。
小径陡峭,布满碎石。刘寅每走一步都得抓紧旁边的灌木或岩石。虚弱加上饥饿,让他眼前阵阵发黑。洪国玉和陈老栓互相搀扶着,翠儿抱着孩子,走得更加艰难。
“啊!”身后传来一声惊叫。
刘寅回头,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脚下一滑,滚下了山坡。好在坡不陡,她滚了几圈就被一棵小树挡住,但已经吓得脸色惨白,手臂擦伤流血。
“扶她起来。”张彤下令。
李石头和一个年轻男人下去把她搀上来。队伍停下来,气氛更加压抑。
“这样走太慢了。”王疤眼烦躁地说,“天黑前进不了山,都得冻死在路上。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张彤冷冷地问。
“分两拨。”王疤眼说,“能走的,跟着我先上去探路,找落脚点。老弱慢点走,后面跟上。”
刘寅心里一紧。这分明是想甩掉累赘,甚至可能…
“不行。”刘寅果断拒绝,“分开了更危险。山里情况不明,万一遇到土匪或者野兽,人少就是送死。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王疤眼瞪着眼。
刘寅看向张彤:“张兄,你经验丰富,你觉得呢?”
张彤沉思片刻:“不能分。但得加快速度。”他看向那几个最虚弱的,“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,只带水和一点吃的。互相搀扶,谁走不动了说一声,大家轮流背。”
这方案虽然残酷,但现实。几个老人默默解下身上仅有的包袱——里面不过是几件破衣服,或者一点舍不得吃的草根树皮。
队伍继续前进。刘寅感觉肺像要炸开,喉咙里全是血腥味。但他不能停,他知道,一旦停下,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又走了一个时辰,小径开始平缓,进入一片相对开阔的山坳。这里树木稍密,地上有厚厚的落叶。最重要的是,刘寅听到了水声——虽然微弱,但确实是流动的水声。
“有溪流!”洪国玉也听到了。
人们精神一振,脚步加快了些。转过一个山角,一条细细的山溪出现在眼前。溪水清澈,从石缝间潺潺流出,在下游汇成一个小水潭。
“水!”有人欢呼着扑过去,趴在水边就喝。
“等等!”刘寅急忙阻止,“不能直接喝生水!”
但已经晚了。几个人已经灌了几大口。刘寅叹了口气。他知道,在这个时代,干净水源的概念几乎不存在。但他更知道,未经处理的山溪水可能含有寄生虫卵、细菌,对虚弱的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。
“烧开了再喝。”刘寅大声说,“不然会生病!”
喝了水的人茫然地看着他,显然不理解。
张彤走了过来:“听他的。刘兄弟懂医术,他说不能喝,就有道理。”
这话起了作用。人们停下动作,眼巴巴地看着溪水。
刘寅指挥洪国玉和李石头用石头垒了个简易灶,架上瓦罐烧水。他则沿着溪流往上走了一段,仔细观察。
溪水确实清澈,源头应该是山泉,相对干净。但水潭下游,他看到了一些动物的粪便,还有腐烂的树叶。直接喝确实有风险。
烧水需要时间。趁着这个间隙,刘寅开始观察周围环境。
山坳三面环山,只有他们来的那条小径可以进出,易守难攻。地势相对平坦,有大约两三亩的荒地,长满了杂草和灌木。溪流可以提供水源,虽然不大,但应该不会完全干涸。最重要的是,刘寅在溪流对岸的岩壁上,看到了一些特殊的东西。
黑色的,层状的岩石。
他心跳加快了。是页岩?还是…煤?
他小心翼翼地踩着石头过溪,走到岩壁下。黑色的岩层大约有一尺厚,夹在灰白色的砂岩中间。他捡起一块脱落下来的黑石,入手沉重,表面有油脂光泽。用指甲划一下,留下黑色痕迹。
是煤。虽然品质可能不高,但确实是煤。
露天煤矿。
刘寅的手微微发抖。有了煤,就有了稳定的燃料。可以烧水、取暖、煮饭,更重要的是——可以冶炼!
冶铁需要高温,木炭能达到,但煤的热值更高,而且可以炼焦,得到更好的冶金焦炭。如果能找到铁矿…
“刘兄弟,你看什么呢?”洪国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刘寅深吸一口气,转过身,尽量平静地说:“洪兄,你看这黑石头。”
洪国玉接过石头看了看,又用鼻子闻了闻:“这是…石炭?我听说有些地方烧这个,烟大,呛人。”
“对,是石炭。”刘寅点头,“但如果我们有办法处理,它能烧得很旺,比木柴耐烧得多。”
洪国玉眼睛亮了:“你的意思是…”
“我的意思是,”刘寅压低声音,“这地方,有水源,有平地,还有燃料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些吃的,或许真能在这里扎下来。”
洪国玉环顾四周,激动得嘴唇哆嗦:“可…可这地能种吗?石头这么多。”
“开荒难,但不是不能。”刘寅说,“而且,我们不一定全靠种地。山里可能有野物,有野菜,还可以…做点别的。”
“做什么?”
刘寅没回答。他看向溪流,看向远处的山峦,心中一个计划正在慢慢成形。
但首先,他们得活过今晚。
第三节 夜袭
天黑得很快。
秦岭的夜晚,温度骤降。虽然已经是三月,但山里的夜风依然刺骨。火堆成了唯一的温暖来源。
张彤安排人轮流守夜。第一班是他自己和刘寅,第二班是王疤眼和赵四,第三班是洪国玉和李石头。其他人挤在火堆旁,用仅有的破布和草叶裹着身体。
刘寅坐在火堆边,添着枯枝。张彤提着刀,在营地周围慢慢巡视。月光很淡,被云层遮挡,只有星星点点的光洒下来,勉强能看清几丈内的轮廓。
营地选在山坳中央,背靠一块巨大的岩石,前面是溪流,左右相对开阔。张彤说这个位置不容易被偷袭,但也强调不能完全放松警惕。
“张兄,”刘寅等张彤巡视回来,低声问,“你的伤怎么样?”
张彤在火堆旁坐下,解开绷带。伤口依然红肿,但似乎没有继续恶化。“还死不了。”他淡淡地说,“你白天说的草药,是什么样子的?”
刘寅根据记忆描述了几种可能有抗菌作用的草药:蒲公英、金银花、鱼腥草…但他不确定这个季节、这个海拔能不能找到。
“明天我找找看。”张彤说,“你懂的可真多。不像个普通读书人。”
刘寅苦笑:“家里杂书看得多罢了。张兄,你说…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?”
张彤沉默了一会儿,看着跳动的火焰:“看运气。如果真有野物,能撑几天。但如果找不到吃的,三天,最多五天,就得继续走。”
“我不想走了。”刘寅说。
张彤转头看他。
“这里有水,有柴,还有石炭。”刘寅指着煤层的方向,“我想试试,能不能在这里建个…家。”
“家?”张彤笑了,笑容里满是苦涩,“这年头,哪还有家。”
“没有就建一个。”刘寅的声音很轻,但很坚定,“张兄,你当过兵,知道怎么训练人。洪兄弟识字,能管账目。我…我有些特别的想法。我们三个,加上这些人,或许真能在这山里活下去,而且活得比别人好。”
张彤盯着刘寅看了很久,火光在他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。
“你想当山大王?”他问。
“不。”刘寅摇头,“我想建一个地方,让跟着我的人不用再饿肚子,不用再被人欺负。我想定下规矩,让大家按规矩活。”
“规矩…”张彤咀嚼着这个词,眼神复杂,“朝廷有规矩,结果呢?”
“所以我们的规矩得不一样。”刘寅说,“简单,公平,让大家觉得遵守规矩对自己有好处。”
张彤没说话,只是慢慢磨着刀。刀刃在石头上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。
“先活过今晚吧。”最终他说。
午夜时分,换班了。
王疤眼和赵四来接替。刘寅回到火堆旁躺下,身体累极了,但大脑却异常清醒。他听着溪流的潺潺声,听着周围人粗重的呼吸和鼾声,听着山林深处隐约的兽鸣。
突然,他听到了一点异样的声音。
不是风声,不是水声,而是…极其轻微的,踩碎枯叶的声音。
刘寅猛地睁开眼,侧耳倾听。声音是从营地西侧传来的,离他们大约二三十步远。
他悄悄推了推身边的洪国玉。洪国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,刘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,指了指声音来的方向。
洪国玉瞬间清醒,紧张地看向那边。
守夜的是王疤眼和赵四。王疤眼靠在一块石头上,似乎睡着了。赵四坐在火堆边,低着头打瞌睡。
脚步声越来越近,不止一个人。
刘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悄悄摸到张彤身边,轻轻推他。张彤立刻睁开眼,眼神清明,完全没有睡意。
“西边有人。”刘寅用口型说。
张彤点点头,慢慢坐起来,手按在刀柄上。他朝王疤眼那边看了一眼,眉头皱紧。
就在这时,西侧的灌木丛突然动了!
三个黑影猛地窜出来,直扑火堆旁熟睡的人群!
“敌袭!”张彤大吼一声,拔刀跃起。
几乎同时,王疤眼和赵四也惊醒了。王疤眼抄起短棍,赵四举着柴刀,但反应慢了半拍。
那三个黑影目标明确——扑向翠儿怀里的孩子!显然,在他们眼里,孩子是最容易得手、也最“可口”的“食物”。
翠儿尖叫起来,死死抱住孩子。
刘寅想都没想,抓起身边一根燃烧的柴火,猛地朝最前面的黑影砸去!
燃烧的柴火砸在那人脸上,火星四溅。那人惨叫一声,捂着脸后退。另外两个黑影愣了一下。
就这一瞬间,张彤的刀到了!
刀光在夜色中划出一道寒芒,劈向第二个黑影。那人反应极快,就地一滚,躲开了要害,但肩膀被划开一道口子,鲜血喷溅。
第三个黑影见势不妙,转身要跑。王疤眼这时终于反应过来,一棍砸在那人腿上。咔嚓一声,腿骨断裂的脆响在夜空中格外刺耳。
战斗在十几秒内结束。
三个袭击者,一个被烧伤脸,一个肩膀受伤,一个断了腿,全都失去了战斗力。
火堆被重新拨亮。人们惊魂未定地围过来,看清了袭击者的模样。
是三个男人,都瘦得皮包骨,衣衫褴褛,手里拿着削尖的木棍。烧伤脸的那个年纪较大,约莫四十多岁,另外两个年轻些。他们倒在地上,恐惧地看着围上来的人。
“是…是吃人队…”陈老栓哆嗦着说。
张彤提着刀,刀尖还在滴血。他走到那个断腿的人面前,用刀挑起他的下巴:“你们是哪部分的?还有多少人?”
断腿的人疼得龇牙咧嘴,但咬着牙不说话。
王疤眼上前,一脚踹在他断腿处。那人惨叫起来。
“说!不然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!”
“就…就我们三个…”那人终于开口,声音嘶哑,“没…没别人了。我们也是逃难的,饿…饿疯了…”
刘寅看着这三个人。他们眼中是野兽般的饥饿和绝望,但也有一丝残存的人性——此刻是深深的恐惧和求生的渴望。
“杀了他们。”王疤眼说,“留着是祸害。”
“对,杀了!”赵四附和。
几个惊魂未定的流民也喊起来。
张彤没说话,只是看向刘寅。
刘寅知道,这是考验。如果他表现得软弱,不仅王疤眼会看不起他,张彤可能也会怀疑他的领导能力。但如果真杀了这三个人…他来自现代的道德观念无法接受。
更重要的是,杀人容易,但后果呢?这三个人也是被饥饿逼疯的可怜人。而且,他们现在急需劳动力…
“不能杀。”刘寅开口,声音不大,但很清晰。
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“他们也是人,也是被逼的。”刘寅说,“杀了他们,我们和吃人队有什么区别?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王疤眼冷笑,“放了他们?让他们回去报信,带更多人来找我们?”
“不放。”刘寅走到那个年纪较大的烧伤者面前,蹲下身,“你们想活吗?”
烧伤者惊恐地看着他,点了点头。
“想活,就跟着我们。”刘寅说,“但我们有规矩。第一,不准吃人。第二,听话干活。第三,敢有异心,死。”
他转向张彤:“张兄,你看呢?”
张彤盯着刘寅看了几秒,然后点头:“可以。但得绑起来,盯着。观察几天,如果老实,再松绑。”
“这不妥吧?”王疤眼反对,“万一他们夜里…”
“夜里分开关,轮流盯着。”刘寅说,“另外,他们的食物减半,直到证明忠诚。”
这是折中方案。既展示了仁慈,也保留了威慑。
王疤眼还想说什么,但看到张彤已经同意,只好哼了一声,不再反对。
三个俘虏被用草绳绑起来,拴在营地边缘的大石头上。断腿的那个,刘寅用树枝做了简易固定——虽然简陋,但至少比不管强。
处理完俘虏,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
这一夜,没人再睡得着。
第四节 晨议
清晨的山坳,雾气弥漫。
溪流的水汽和山间的晨雾交织,将营地笼罩在一片朦胧中。火堆早已熄灭,只剩下余烬和几缕青烟。
刘寅几乎一夜没睡。他靠在大石头上,看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,看着雾气中逐渐清晰的群山轮廓。
昨晚的事,让他深刻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残酷。也让他明白,要想活下去,不能只靠仁慈和理想,必须有武力,有组织,有纪律。
张彤走了过来,在他身边坐下。左臂的绷带又渗出了血,但他似乎毫不在意。
“你昨晚做得对。”张彤说,“但不夠狠。”
刘寅苦笑:“我知道。但在我的…理念里,人不该轻易杀人。”
“理念?”张彤咀嚼着这个词,“这世道,理念填不饱肚子,也挡不住刀。”
“但理念能让人团结。”刘寅说,“如果我们和那些吃人队一样,见了弱者就抢,见了活人就杀,那我们和野兽有什么区别?就算活下来,也只是多了一群野兽。”
张彤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你说得对。我以前在军中,见过太多…兵不像兵,匪不像匪。朝廷发不出饷,当兵的就抢百姓,百姓活不下去就造反,造反了朝廷又派兵剿…没个头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不一样。”刘寅说,“我们要定下规矩,让大家明白,跟着我们有饭吃,有活路,但必须守规矩。规矩保护大家,也约束大家。”
张彤点点头:“具体怎么做?”
刘寅想了想:“第一,所有食物集中分配,按劳分配,多劳多得,但保证每人最低口粮。第二,建立轮值守夜和巡逻制度,张兄你负责训练和指挥。第三,明确分工:有人负责打猎找食物,有人负责建住处,有人负责找水和燃料。”
“那三个俘虏呢?”
“观察三天。如果老实,就纳入分工,但暂时不给武器。如果表现好,逐步给予信任。”
张彤沉吟片刻:“可以。但得有个名头。咱们这群人,得有个称呼。”
刘寅早有想法:“叫‘铁山营’如何?我们在铁山之中,也要有铁一样的纪律和意志。”
“铁山营…”张彤重复了一遍,“行。我是营头,你是…军师?”
“叫参谋吧。”刘寅说,“我出主意,你做决定。”
这是明确的权力划分。刘寅知道,在乱世中,军事指挥权必须集中,而张彤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他自己则负责战略规划和制度建设。
两人正说着,洪国玉也走了过来,脸色疲惫但精神尚可。
“刘兄弟,张大哥。”他坐下,“我算了一下,咱们现在总共三十七人,能干活的男人…算上那三个俘虏,十五个。女人十个,孩子老人十二个。食物…昨晚把最后的干粮都分完了,今天再找不到吃的,就得饿肚子。”
严峻的现实。
刘寅看向溪流对岸的煤层:“今天分三组。第一组,张兄带队,带几个男人去打猎,找野物,也看看有没有野菜野果。第二组,洪兄带队,带女人和老人,沿着溪流往下游走,找更大的水源,也看看有没有能吃的植物根茎。第三组,我带着李石头和两个还能动的俘虏,去挖石炭,顺便看看周围地形。”
“挖石炭做什么?”洪国玉问,“那东西烟大,不好烧。”
“我有办法处理。”刘寅说,“而且,石炭能烧高温,以后有用。”
张彤站起身:“那就这么定。王疤眼他们呢?”
“王疤眼跟你去打猎。”刘寅说,“他自称打过猎,应该有些本事。赵四和另一个跟着洪兄。他们三个还是得分开,互相牵制。”
张彤点头:“行。我去召集人。”
晨雾渐渐散去,阳光透过云层,洒在山坳里。新的一天开始了,也是铁山营正式运作的第一天。
人们被叫醒,张彤宣布了分组和任务。听到有具体的分工,迷茫的人群似乎有了一点方向。虽然依然饥饿,但至少有了事做。
王疤眼对分配没有异议,只是问:“打猎的武器呢?就一根棍子一把刀?”
张彤解下腰间的弓——那是一把简陋的单体弓,弓弦都快断了:“我还有这个,但箭只剩三支。”
“我看看。”王疤眼接过弓,试了试弦,“弦不行了,但还能用。箭不够,可以削竹箭。另外,可以做几个套索陷阱。”
刘寅心中一动。王疤眼确实懂打猎。
“王大哥,打猎就拜托你了。”刘寅说,“打到东西,按功劳分配,你多分一份。”
王疤眼咧嘴笑了:“这话中听。”
分组完毕,各自出发。
刘寅带着李石头和两个俘虏——那个烧伤的叫老吴,另一个肩膀受伤的叫二狗——来到煤层前。断腿的俘虏留在营地,由翠儿和陈老栓看着。
“挖这些黑石头。”刘寅示范用木棍和石块撬动岩层边缘松动的煤块,“小心别塌了。”
李石头很卖力,两个俘虏也不敢怠慢。很快,他们就挖出了一小堆煤块,大约几十斤。
刘寅观察着煤的品质。含硫量可能不低,燃烧会有异味,但热值应该不错。他需要做个简单的焦化实验——把煤隔绝空气加热,得到焦炭和煤焦油。焦炭是更好的燃料,煤焦油则能提取出有用的化学物质。
但现在条件太简陋了。他需要黏土做坩埚,需要鼓风装置…
一步一步来吧。
挖煤间隙,刘寅让李石头在周围转转,看看有没有黏土,或者铁矿石的迹象。他自己则爬上一块较高的岩石,俯瞰整个山坳。
从高处看,地形更清晰了。山坳呈葫芦形,他们现在在葫芦底部,地势相对平坦。葫芦口就是他们进来的小路,狭窄易守。山坳深处,溪流蜿蜒向上,消失在密林中。那里可能有更大的水源,也可能通向更深的山。
是个好地方。
如果能在这里站稳脚跟,开垦荒地,建立防御,或许真能成为一个根据地。
但首先,还是食物。
中午时分,三组人陆续回来。
张彤那组一无所获。王疤眼下了几个套索,但还没收获。只找到一些苦菜和野葱,数量很少。
洪国玉那组稍好。在下游两里处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水潭,水边有一种叫“水芹菜”的野菜,采了不少。还抓到了几只青蛙和几条小鱼——用衣服当网捞的。
刘寅这组的煤挖了不少,但没有食物。
所有收获放在一起:一小堆野菜,几只青蛙,几条手指长的小鱼,几把野葱。
三十七个人分。
“先煮一锅野菜汤,大家喝点热的。”刘寅说,“青蛙和小鱼留给今天功劳最大的几个人。”
没人反对。人们眼巴巴地看着那口破瓦罐,看着野菜和水在罐中翻滚。
汤很稀,几乎就是盐水煮野菜。但每个人都喝得小心翼翼,像在品尝珍馐。
刘寅喝着自己那份,胃里依然空得难受,但至少有了点暖意。
下午,继续分工找食物。
王疤眼提议去更远的山坡看看,那里可能有野兔的洞穴。张彤同意了,带着王疤眼和另外两个男人去了。
刘寅和洪国玉留在营地,开始规划下一步。
“刘兄弟,光靠找野食不行。”洪国玉忧心忡忡,“这么多人,每天消耗太大。野菜总有挖完的时候,野物也不稳定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刘寅说,“所以得开荒种地。但现在没种子,没农具,季节也不对。得先想办法度过这几个月。”
“你有什么想法?”
刘寅看向煤堆:“我想试试烧陶。有了陶器,可以储水,可以煮饭,也可以…试着炼铁。”
“炼铁?”洪国玉瞪大了眼,“那得要铁矿石,要高炉,要鼓风…咱们哪有那条件?”
“一步一步来。”刘寅说,“先找铁矿石。秦岭有铁矿,我知道大概的地质特征。找到了,哪怕是小矿脉,也能炼出铁来做工具。有了工具,开荒就快了。”
洪国玉被这个大胆的想法震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说:“刘兄弟,你…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?这些想法,不像个普通读书人。”
刘寅看着远处起伏的群山,轻声说:“我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。那里的人,曾经也经历过苦难,但他们靠知识和勤劳,建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。我想在这里,试试能不能也做到。”
洪国玉听不懂,但他能感受到刘寅语气中的坚定和某种…超越时代的眼光。
“我跟你干。”洪国玉说,“反正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。”
傍晚,张彤那组回来了。
这次有了收获——一只野兔,两只山鸡。王疤眼用套索捉到的。
营地沸腾了。
虽然一只兔子两只鸡对三十七个人来说还是太少,但这是实实在在的肉。
肉被小心地处理,和剩下的野菜一起炖了。每个人分到一小块肉,几口汤。
但就是这一小块肉,让人们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。
饭毕,张彤召集所有人。
“从今天起,咱们就是铁山营。”张彤站在火堆前,声音洪亮,“我是营头,刘寅是参谋,洪国玉管账目。规矩很简单:听指挥,守纪律,多劳多得,不准内斗,更不准吃人。违反的,轻则饿饭,重则处死。听明白了吗?”
人们稀稀拉拉地应着。
“大声点!听明白了吗?”张彤喝道。
“明白了!”这次声音整齐了些。
“好。”张彤说,“今晚继续轮值守夜。明天,继续找吃的,开始建窝棚。咱们要在这里,活下去!”
“活下去!”有人跟着喊。
“活下去!”
声音在山坳中回荡,惊起了林中的飞鸟。
刘寅站在人群中,看着那一张张被火光映照的、瘦削而坚定的脸。
这是铁山营的第一天。
艰难,饥饿,前途未卜。
但至少,他们有了一个名字,有了一个目标。
活下去。
然后,活得更好。
夜色渐深,群山沉默。
刘寅躺在简陋的草铺上,看着满天星斗。
他想起了实验室的灯光,图书馆的书架,导师的叮嘱。
那些都远了。
现在,他在这里,在崇祯八年的秦岭深处,带着三十多个绝望的人,试图在乱世中开辟一条生路。
前路漫漫,危机四伏。
但他没有退路。
只能向前。